黨國一體的文化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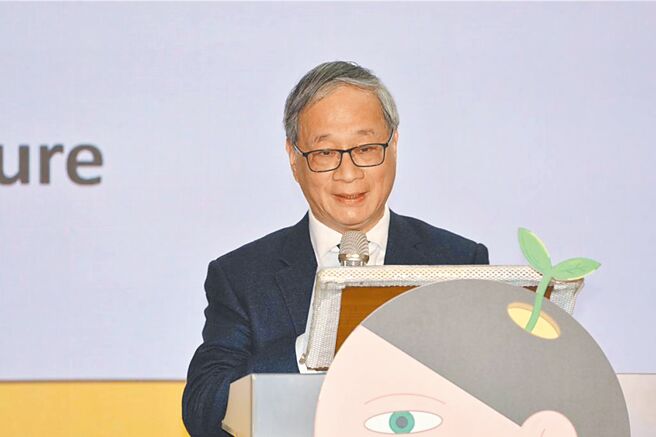
(圖/本報系資料照)
文化部長李遠在預算被刪減後,一度引述在日本側翼言中之「破蛋說」,還哽咽說臺灣文化主體性的「胚胎」在此關鍵時期被「下毒手」云云。看了這一段,我有點驚訝,難道少了些官方預算,所謂「臺灣文化」的主體性無法撐住?
國家的公關絕對不等於執政黨的政治宣傳,可是傳統的中國黨國體制下,執政黨掌握絕對權力,黨的價值凌駕一切,黨代表國家行使主權,並且全面控制國家機器。黨國即以黨治國,國庫同黨庫被視爲理所當然,曾擔任過國民黨黨營事業高幹的無黨籍部長李遠,在回答立委質詢時說出「我們民進黨」,其心態昭然若揭,沒錯,民進黨當局竟是黨國體制的劣質複製品一個。
確實,民進黨當局,特別是前國民黨文官體系出身的蔡英文執政後,透過官方單位分配資源的方式,拉攏文化傳媒界,包括捏造虛假的歷史解釋的手法在內,試圖全面掌握歷史詮釋權。例如,先前公視拍攝的《聽海涌》,假藉敘述日本戰敗後的臺籍日本兵戰犯的故事,催化臺人的自憐情緒,凝聚基於受害者意識的「臺灣認同」來對抗虛擬的「可惡中國」(可惜,其藝術性和文化涵養遠不如閩南傳統的哭調)。
電影也好,連續劇也好,這種服務「1624『世界島』迷幻」奇葩史觀的內容,感覺這幾年拍得不少。不少文化界人士,爲了拿到官方賜給他們的經費或好處,想盡辦法迎合當局的價值,忖度揣摩執政者的偏好。如此做出來的作品與大陸的央視或朝鮮中央電視臺所播出的內容,其本質和脈絡上沒有很大的差別。這些爲了爭取好處,而主動迎合民進黨自憐史觀的臺灣文人,沒什麼資格嘲笑平壤的李春姬了。換言之,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話語精神是,不管姓資的還是姓社的,看似對所有掌權者來講,還滿實用的。
那麼,這些被當局灌輸的價值會走上什麼樣的結局呢?日本作家鈴木明,四十幾年前出過《愛國》一書,裡頭提到鈴木訪臺時,與當地嚮導之間的對話。鈴木問當年50歲左右,日語流利的男性導遊(似臺灣本省人)說:在臺灣什麼樣的人在聽披頭樂團的音樂?男導遊笑道:那些只有學生等小鬼聽的,那些小鬼,其實什麼都不懂,因爲頭腦單純,學校教什麼「愛國」,就深信爲了國家赴大陸作戰。我年輕時(日據時代)學校老師鼓吹我們「忠君愛國」,跟那個一樣」。男導遊不忘補一句話:「我們在大東亞戰爭時已上過一次日本的當,說什麼「爲了國家」,我們再也不會上這個當,大家已都知道這不過是個騙局。可是,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,我完全搞不懂。反攻大陸、披頭、愛國?真奇怪啊!我完全搞不懂這些小鬼長大了以後會變如何?
當年被譏諷頭腦單純的那些小孩們大了以後,也許還在繼續聽披頭的歌,但一個都沒上去過反攻大陸的戰線,當年的愛國情操老早消失了。同理,現在當局花一大筆錢灌輸的價值,若沒帶真實的生命,也不產生實際利益的時候,有一天遲早會被丟進水溝裡。(作者爲旅臺資深日本媒體人)













